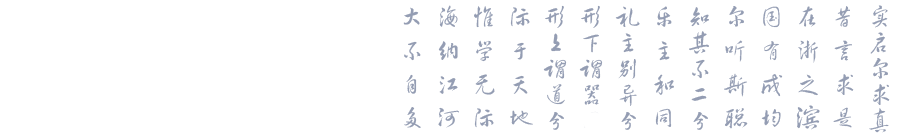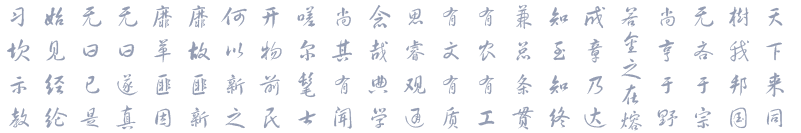1938年11月19日,抗日战争中西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主持的校务会议上,正式确立“求是”为校训,这是浙大116年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事件。
浙江大学1938年9月三迁到达广西宜山,在宜山遭遇了疟疾疫病和日寇狂轰滥炸双重灾难。那是浙大西迁路上形势最严峻,困难最深重,师生员工人心最动荡的时期。而竺可桢校长刚刚在短短的十二天里,在泰和失去了相濡以沫18年的爱妻和最钟爱的次子,身心遭受沉重打击,真可谓“内外交困”。
但竺校长却以超群的坚强意志和缜密卓绝的智慧,为浙大找到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克敌制胜的宝贵武器———“求是”校训,并在多次讲话和著作中,反复阐明求是要义。其中,《王阳明先生和大学生典范》、《求是精神和牺牲精神》、《科学之精神与方法》是竺可桢论述“求是”校训的经典名篇。
竺可桢特别推崇王阳明“君子之学,岂有心於同异,惟其是而已”的理念和“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的论述,他强调“本校推原历史的渊承,深维治学的精义,特定‘求是’二字为校训,阳明先生这样的话,正是‘求是’二字的最好注释,我们治学做人的最好指示”。
七十五年来,“求是”校训一直是浙江大学的精神支柱。1979年4月,刚刚兼任浙江大学校长的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在就职演说中,向全校师生员工提出:“要继承和发扬‘求是’精神,培养和鼓励‘创新’精神”。
钱三强说,“求是”是我们浙江大学的“祖传”,因为浙大的前身就是1879年建立的“求是书院”。但是,从我们现在的情况和将来的任务出发,仅做到“求是”就不够了,要特别提倡在“求是”的基础上“创新”,就是要求同学们从现在起养成习惯,以适应不断发展的需要。他还举了澳大利亚的昆虫学家找到一种俗称“屎壳郎”的甲虫解决了牛粪灾害,促进养牛业发展和法国的建筑师用钢筋水泥加一层橡皮,减少地震波的传导,避免地震对高层建筑物的破坏这样两个生动的创新例子,说明创新虽不容易但也并不神秘。
1988-1995年,路甬祥院士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特别重视校风建设,在他主持下,沿承钱三强校长强调“求是创新”的倡议,并将其具体表述为“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1992年,路甬祥在纪念建校95周年的致辞中指出:“创新(即创造)精神,严格地说,它已包含在求是精神之中,……但人们往往把求是理解为求实,侧重于对现有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对现状的客观分析和把握,而不特别强调创造与创新,……创新,正是历史上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杰出人士的共同特点。浙江大学要办得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特点……必须十分重视创新精神的提倡。”路甬祥还题写了“求是系治学之本,创新乃科技之源”的著名题词。
以“求是创新”为新时期浙江大学校训,是对“求是”的继承与发展,赋予浙大校训更加清晰、充实、丰富的内涵与时代特色。浙大校训由“求是”发展为“求是创新”,是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必然。曾任浙大校长11年,现任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的潘云鹤院士就强调,创新已成为时代的关键词,“由创新,可以想到与自然科学相联的发现,与工程相联的发明,与文学艺术相联的创造。……‘求是’要求求深,‘创新’要求求新,‘求是创新’是一个很好的校训,与浙大注重综合性、研究性、创造性的办学目标相吻合,能够指导大学学习、研究、创造这三种基本活动”。
“求是”精神是浙大举校西迁,历经艰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概括与总结,是浙大西迁文化的精髓,是以竺可桢为代表的老一代浙大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珍贵遗产。现在,“求是创新”已是浙江大学的旗帜和品牌,是浙大百年文化的灵魂,是浙江大学持续发展的永恒动力源泉,也是所有浙大人共同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