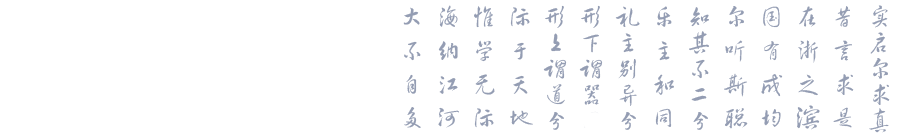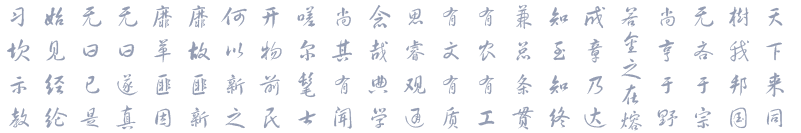1938年10月底,西迁中的浙大所有师生全部安抵宜山,并于11月1日开学上课。1939年11月25日,日军长驱直入,南宁陷落,浙大决定于次日筹备再次搬迁。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竺可桢校长在1939年5月15日星期一(晨阴)的日记中写道:
“八点一刻至校,接教育部公文,准本校成立农化系,又于暑期中迁移入黔。同时迪生来电谓教部已准浙江设立战时大学,更名为英士大学。此全系一种投机办法,因教部长陈立夫系陈英士之侄也。许绍棣等之不要脸至此已极,可谓教育界之败类矣。专设医,工,农三学院而无文理,焉望其能办好!接宋楚白〔函〕,知三号倭机炸重庆,……仅曾家岩、上清寺及城内武库街至校场口、小梁子、会仙桥、小什字等未遭殃而已。四号死伤达一万人云。……”
这段日记记载中,竺公的忧校、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日记的下半段写道:
“三点至校,土木系四年级生陈叔陶来。陈在二年级时即研究历史上之文学,傅孟真(即傅斯年-作者注)认为有价值。前次在昆明余曾询孟真有否嘱其入历史研究所之可能,孟真以为如渠志愿在于研究历史,甚愿罗致之。今日陈来,据云渠已得傅孟真来函招其往史语所,渠之志愿仍在土木机构方面,不愿往。余告以国内无一机关可以研究此学,土木系毕业而后只可在路上作测量工作而已,故嘱其于路上工作一年后仍能专心历史。”
竺校长在国家危难、民族危急和浙大危亡之际,可谓百事操劳、殚精竭虑,但仍在日记中,以二百多字的篇幅,记载对陈叔陶这个学生前途命运的关切,字里行间透溢着爱生如子之真情。
陈叔陶(1913-1968),浙江余姚人。1932年由杭州高级中学毕业,考取上海交通大学和浙大,后入交通大学读书。入学不久患病休学,1934年以保留学籍资格入浙大土木系。在休学期间,以高中毕业生的学历,用文言文写了一本《新元史本证》专著,指出了新元史中23处错误。
20世纪30年代在杭州学习时的陈叔陶 20世纪60年代在西安工作时的陈叔陶
陈叔陶著《新元史本证》
我国《二十四史》中的元史由明宋濂编写,民国初年,学者柯绍忞又写了一本新元史。历史学界认为新元史写得比旧元史好。陈叔陶长兄陈登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的毕生巨著,近300万字的《国史旧闻》,在学术界的深刻影响延续至今。陈叔陶在病休期间,写作《新元史本证》,显然受到乃兄治史的影响,但从目前所知的文字材料中,未找到乃兄对他的指导和教正。陈叔陶对照有关元史的其他资料,经慎重考证,发现了新元史的23处失误。其中有:人名、地名、纪年、纪日、纪事、世系、封爵、官职、氏族、谥号11处“多误”;纪年、纪事、宗室、世族、姓氏共5处“多遗”;重叠重复、译音无定、误氏为人、体例不一、书法未审、剪裁未当、人名未当7处。据他的查证和确凿的史实,他写了7万字的《新元史本证》一书,投寄给当时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语言研究所自1928年起,每年出集刊一“本”,每本四“分”。为集刊撰搞的有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胡适等史学家和赵元仁、李方桂等语言学家。名人荟萃的集刊,收到名不见经传的年青学生陈叔陶的专著,其内容的精炼和准确,评论论据之无懈可击,立刻引起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郑重关注。
傅斯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五四运动的主将之一,后曾任台湾大学校长。根据陈叔陶论文函发落款地址是浙江大学的线索,傅斯年致信竺可桢,请他查询陈某是何许人也。竺校长自然先在历史系的教授和教师中寻找,再从历史系高年级学生中查看,均无音信。竺可桢先生难以想象,这本评史力作竟然出自时为高中毕业学生,现为浙大土木系二年级生的陈叔陶之手笔,实属难能可贵,竺公对此事印象深刻。出于爱才之心,竺可桢在陈叔陶即将由浙大土木系毕业前夕,召见这位在四年前撰写佳作的“史学奇才”,询问他毕业后的志向,并在之前询问过傅斯年所长接受陈叔陶入语言所之可能,竺校长告曰“土木毕业后,只可在路(指施工造路)上作测量工作而已”之语,实为竺公推心置腹坦陈之言,不是爱才心切,以一校之长的身份,他绝不会说出似有贬土木而扬史之语,可谓用心良苦也。
陈叔陶虽治史有心,但仍志在所学专业。他在1939年毕业后,先后担任昆明桥梁设计处工务员,浙大龙泉分校讲师,中山大学副教授。1950年任西北工学院教授,后任西安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参与北京十大建筑、广州电视塔方案评审,为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专家组成员,1958年任中苏合作预应力钢结构研究课题组长;领导题课参加国防科委防护结构研究和计算任务;对原极及原壳在冲击载荷作用下的结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结合教学和科研实践,写出30多篇在钢结构、结构力学、弹性力学等领域有所创见的论文,被选为陕西省力学学会副理事长,成为杰出的力学家。在他于1968年5月22日病逝前几年,他为培养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青年教师,抱病在三年中编写了100万字的讲义和几十万字的弹性力学教材,为全校中青年在节假日讲课三年,分文不取。终因久病和积劳之疾,陈叔陶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年55岁。
陈叔陶多次被评全国劳动模范,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一次全国劳模大会期间,他和与会的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相遇,竺公一眼就认出这位当年他十分中意的门生。师生二人回忆当年竺公日记所载之经历,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不胜感慨系之。
193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07本第3分刊登的文章和作者是:
陈寅恪,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陈叔陶,新元史本证;俞大纲,纪唐音统签;孙楷第,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李家瑞,内说书变成戏剧的痕迹。
当年,陈叔陶是23岁的青年人,名列这些史学大师之列,是“后生可畏”之生动实例;他英年早逝,但他的名字在集刊上永垂不朽。
作为浙大学生,陈叔陶青年评史,为浙大提高了声誉,自然让竺校长和浙大师生感到欣慰。陈叔陶与浙大的情份远非仅此,他的四弟陈季涵也是浙大学生,而且是兄弟同班的同学。他大哥的长子,即他的长侄陈宜张,在他兄弟们指导自学高中课程后,考取四所国立大学,因二位叔叔均是浙大学生,而最后“随亲择校”于1946年进入浙大医学院,成为首届毕业生,在至今的60多年中,他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的科研硕果和出任四校合并后新浙大医学院首任院长所作出的贡献,为陈家和浙江大学的不解之缘,写下了浙大校史上的一段佳话。
注:《竺可桢日记》第一册(1936-1942)第3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
( 作者:熊家钰,机械系58届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