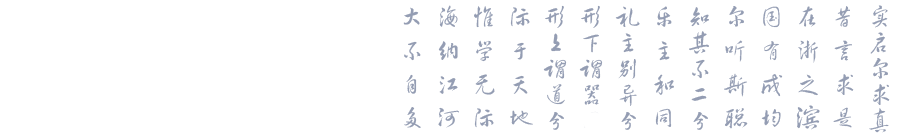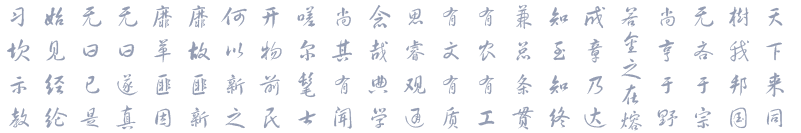【人物名片】沈学年(1906-2002),字宗易,浙江余姚人,我国著名农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耕作学创始人。曾任浙江大学农学院(后改建为浙江农学院、浙江农业大学)教授,曾当选为第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第六届浙江省人大代表、民盟浙江省委第一至四届委员。
每当我回忆起沈师,总有几个镜头闪现在眼前。首先是他满头大汗、中气十足的讲课;其次是他赤足下田、抚弄水稻的风采;还有就是他扶掖青年、友善待人的品格。
沈师讲课时易出汗,即使是窗外飘雪的严冬,照样头上大汗淋漓,这汗,衬托着他的连珠妙语,常能使人会意地敞怀一笑。比如,讲到稻米的品质,他说:“晚籼9号烧出来的饭,刚含到嘴里,还来不及嚼,它就自己爬到胃里去了!”这时,他用不着多说,听众似乎已经口含润、韧、香、滑的米饭,品尝并体验到了什么叫优质米的色香味。
沈师有许多学术著作,特别是有不少经典的教材。他是《耕作学》(南方本)的主编。也是中国南方耕作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本来,在中国的农业大学课程里是没有“耕作学”的,是建国初期开始学习苏联增加的新课程。之前,不但没有耕作学,连“作物栽培学”也并非像现在综合成一门课,而是分成稻作学、麦作学、棉作学、食用作物(除稻、麦以外)、特用作物(除棉以外)等等。而实际教学中,育种被剥离出来,成为专门的育种学、还有育种和栽培研究的“方法论”、“生物统计学”或“生物统计与田间试验”。这几门课是农学系的主课。
耕作学既然是从前苏联传来的,由北农大孙渠教授翻译成中文的著名土壤学和农学家威廉斯的著作《耕作学》(其实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书名应该是农作或农业)便成为主要教材。而在南方,浙江农学院是第一批开设耕作学课程的农学院,沈师是主持教授。1956年,他远赴新疆协助农业部举办苏联专家讲习班,使苏联专家的讲学融入了中国,特别是中国南方的元素。同时,也确立了耕作学从祗侧重提高土壤肥力,发展到既重视土壤肥力,更强调耕作制度改革的学术方向。这些内容,正是耕作学(南方本)的立足点。有人戏称学术上耕作学有“北派”与“南派”和“地派”与“天派”。由于沈师从来都不齿学术上派别之争。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的耕作学和苏联“原版”之间,以及南北相互之间,有同有异,互补互融,从而形成耕作学百花齐放的盛况。
沈学年先生有着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功底。他去美国留学归来,先后在浙江上虞五夫水稻试验农场、黄河河曲农场、西北农学院等地指导和研究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教育。在解放前缺乏教材,依靠手刻钢板印教材的情况下,率先编写出版了《作物育种学泛论》教材,并致力于小麦育种。很多人还记得他闲暇居家时常以激昂的高腔放歌绍兴大班的情景,一如其性格之豪放。后来大面积推广的良种“碧蚂一号”的亲本之一“碧玉麦”,就是他从喜爱的绍兴大班戏名“碧玉簪”中移植而来。
在浙江农学院农学系,沈师主攻水稻。我在1954年毕业留校,就做他的助教,也协助他做晚稻育种的科研。可是,沈师不仅做科研,还更关心生产实践。那时浙江省的农学院、农业厅、农科院技术人才荟萃,相互合作默契。每年农业厅召开的全省农业技术总结大会都是由农业厅的王如海、农学院的沈学年、农科院的吴本忠“三巨头”共同主持。会议都要在总结的基础上写出次年的“技术指导纲要”。每年大会沈师都当仁不让,全力以赴,在大会主持、小组讨论、攥写文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当时农学院著名才子游修龄先生也经常参与指导和主要执笔。
每年的盛会,是多少科技人员在基层、田间和农民一起,辛勤劳动、调查、科研的结果。沈师就是所有活动的践行者,他和绍兴东湖农场的胡香泉在研究实践中结下深厚友谊。东湖农场因试验与推广一年三熟高产,名闻全国。浙江省的农作制度改革也在我国南方广泛推广。在1979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上,“浙江省农作制度改革”以研究和推广的重大价值,被授予一等奖。当时,1978年第一次科学大会的得奖项目是没有奖金的,只颁发了署有得奖项目名称和得奖单位的奖状;第二次大会得奖项目有少量象征性奖金,农学院作为主要三个主持单位之一,也分得了一点钱。沈师就与我们这些参与者一起,买点糖吃。既表庆贺、更是勉励和记忆。
沈师在教学、科研等方面,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与农民做朋友,诚心诚意地在实践中学习、向农民学习。这种思想、作风与行动,对我影响至深。省委在浙江农学院蹲点领导四清运动,到最后落实整改措施时,公开征求群众对教改的建议,我提出要在农村建立固定基点,让学生、教师有研究农业、农村、农民,并为农民服务的具体对象和场所。当场得到主持会议的省委宣传部长盛华同志的支持,并说:“就请你组织一个小组,带头下去,怎么样?”我当众毫不犹豫地应承:“好!”。几天之后我们就在萧山农村安下了家,我“高卧”的“床”,就是在一个像如今居民区门卫岗亭那么大的废弃农舍里,往一个空的大水缸上横铺了一块门板。我的第一项“科研成果”,便是协助农民一起研究防止水稻烂秧的技术。并在大幅度减少烂秧的同时,和当地农技站一起,把搭矮棚“尼龙育秧”的技术推广到占当地秧田一半以上。这些“业绩”固然不值一晒,却给了我深深的体验和时刻铭记于心的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以及与农民交朋友,虚心向农民学习的思想和习惯。这个农村基点也是我在文革后期,能够在萧山、海宁二地,一呼百应,试验和推广“水稻两段育秧”,从而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优秀科研奖的“预研究”或前奏。而我至少在4篇已发表的科学论文题目下,在作者中列入了农民的名字。
沈师扶掖青年,虚心诚意与青年人相互学习,也是我辈楷模。在他退休之后,我常去他家,谈说我们运用系统科学观念,从耕作制度研究发展到组织多学科教师进行农业生态系统研究,并在代表杭嘉湖地区的德清农村建立了新的研究基地。我们也被学校批准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农业生态研究所。他听了连声称好,并时常提出一些意见。鼓励我们发展创新。
他从不在青年人面前居功自傲,总是发自内心的给予鼓励。这些方面很自然地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在教学中就时常告诉研究生相互学习的观念,我也的确从研究生的思想品德、介绍新信息或通过讨论得到思路、信息和线索。
沈师一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我毕业以前就知道他是前浙江大学的工会主席,他连续数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有一次,他出差回来晚了,耽误了代表们集体去京的约定时间,他仍然单独赶去北京。他到达人民大会堂报到地点已是半夜,大会堂宴会厅专门为他一人摆了一小桌菜肴,它对我谈到饿极饱啖的情景,还装出了模样,令我大笑不已。但是,他随后又庄重地说:“周总理专门接见了民主党派的人大代表,给我们鼓励,也交代我们责任。我要记在心上”。
实际上,除了人大代表的一般责任外,沈师还另有重要的统战任务。他的长兄沈宗翰曾经是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主席,其影响遍及东南亚;长嫂沈俪英是著名的小麦育种家,她培育的优良品种“俪英三号”等曾经在长江以北广大地域推广种植。宗翰先生去世后,俪英女士移居美国。沈师受统战部之托,专门赴美会晤长嫂,为两岸统一做些工作。另外,宗翰先生的长子沈君山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与连战、钱复等四人并称台湾政坛“四君子”。但沈君山先生于早年就退出政坛,致力于治学与治校。他曾多次往返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也常来华家池探访沈师。这些活动虽然都是默默无闻地进行,却也如实反映了沈师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以及对统一大业的关切。
(作者:王兆骞,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师,浙江大学生态学学科创建人。)